一场“莫名其妙”的“红绿灯恐慌”。
哈佛汉学家孔飞力,曾经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微观史书,叫《叫魂——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》,通过对中国乾隆年间一场莫名兴起的对子虚乌有的“叫魂”巫术的恐慌,以小见大的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心理问题。

而让我莫名想起这本书,是今天早上起来,看到微博上被刷爆了的“新版红绿灯”规则的新闻。

网上一时盛传说:红绿灯要出新版了!从原来简便的“绿行红停”三色灯,变成特别复杂的“九宫格”,不仅看着让人眼花,而且规则颇为麻烦,跟解数学题一样,你一个看不懂,一脚油门下去,12分就没了。

然后网友们开始各种编段子,说这个“新规”怎么不靠谱,以后坚决不敢排在第一个过红绿灯了云云。
但到了下午的时候,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了一些辟谣,先是各地一些交警开始站出来表态,说自己这儿并没有接到这个所谓的“新版红绿灯”规则,而后是南京市某民警发了详细的“有图有真相”的辟谣——这个被骂惨了的“新版红绿灯”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新规,它依据的是2016年指定的国标,2017年下半年就开始实施了。

而该国标中写的很清楚,所谓的“九宫格红绿灯”,仅仅是“特殊组合中”的一类,国标中明确规定了它应只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会适用——换而言之,我们常见的那种三灯红绿灯并没有被废止,“九宫格红绿灯”从来只是一种补充而已。

至于网上盛传的红绿灯要“取消读秒”的手法,也子虚乌有,因为该国标并没有提到读秒,读秒装置是各地交警按照另一套行业标准根据各地情况自行选装的。
其实仔细想想,你会发现,这谣言本身就挺奇怪的——全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十字、丁字、x字路口?如果真像谣言所盛传的那样,要“全国一盘棋”,统一改换那种九宫格红绿灯。且不说司机们受不受得了,这是多大一项工程,各地得花多少钱、忙活多久才能办完?中间又可能带来多少安全隐患呢?
所以这个谣言是严重违背行政常识的,网民们这得是对交规制定者有多么不信任,将其当傻瓜,才能把这种反常识的恐慌传起来?
可是,这个谣言最初到底是哪儿传起来的呢?
查了半天,情况可能是这样的:
前两天的时候,“九宫格”红绿灯的设计者孙正良在某视频平台发了个直播,在抖音开了个直播,讲述他这个设计的原理,并试图说服大家,他的这个设计很“人性化”,(习惯)“只是时间问题”。

但是,充分了解九宫格红绿灯运行规则的孙老师,显然并不太理解网络的运行规则,尤其是抖音的运行规则。
他显然没想过,他近似这个数学题般的红绿灯设计,已经让不少人错闯了红灯,被罚款扣分了。
平素大家被扣了分、罚了款,因为找不到这奇葩红绿灯的设计人,也就默默忍了。但现在,这个倒霉红绿灯的设计者自己上线直播,试图说服你他这个设计没错,只是你看不懂……
那还等什么啊?冤有头债有主啊!于是,孙老师的直播间,顿时化身大型路怒症治疗现场。短时间内就被一群吐槽他的人给冲了。
起初孙老师还想挣扎一下,呼唤大家理性讨论问题。

可抖音哪里是讲理的地方?孙老师不得不先关了评论,而后干脆注销了自己的抖音账号了事。
而意犹未尽的吐槽者们将此事进一步散播,可能是因为孙老师在直播中“新版红绿灯”的表述容易引起误会,传着传着,这个已经颁布很久的红绿灯标准之一,就被误传成了“2022年新版红绿灯统一标准”了。
这应该就是这场风波发生的始末,这就是个以讹传讹的谣言。
就像孔飞力在《叫魂》中指出的,任何恐慌的传播,一定有酝酿它的社会心理因素。同理,“红绿灯恐慌”突然会在今天火的不像话,我们似乎也能说出一点道理:
从一个“模因”来看,“新版红绿灯”这个谣传能火,是因为它满足了信息传播的三个要素。
首先,它确实有相当的“必读性”。
一个人可以什么时政话题都不关心,但只要他今天还要开车或过马路,看到“新版红绿灯被改的很麻烦”这样的报道,他就一定会点看一看。所以这个话题踩在了几乎所有受众都有观看欲的“必读点”上,当然关注度惊人。
其次,这个谣言能给受众提供一种稀缺的“共识感”。
在当今的这个共识撕裂的舆论场上,对几乎一切话题,大家都有分歧:大到俄乌战争、台海局势,小到司马南、卢克文被封,和服女孩该不该骂。这些话题不同人群的观点都针尖对麦芒,十个人恨不得能给你说出八种不同观点来。
但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话题,跟你吐槽“这红绿灯设计的太傻x”,所有开过车、扣过分的人都能迅速达成统一战线,跟着附和一句,而在这种群议汹汹之下,真相到底如何,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。
最终,我想也是最重要的,就是很多人通过吐槽这个“九宫格红绿灯”,发泄了一种共同的情绪。什么情绪呢?一种被管束时的焦虑感。
我是2019年拿的驾照,当时科二考了三次、科三考了三次,一本驾照拖了一年多才拿到。不过在漫长的考试煎熬中,我特别有兴趣的去重读了一本名著——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。

是的,考驾照这事儿,很容易让我想到《社会契约论》中的某些讨论。因为在我看来,交通规则的形成,其实就是一种自由人们如何达成社会契约的模拟实验。
正如卢梭说“人生而自由”,人们开车上街,归根结底,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得一种想去哪儿去哪儿的“出行自由”。
换而言之,正如所有人都是为了享受自由而不是被管束而参与公共生活的,所有人是为了享受自由而开车的。在这个世界上,认为“某国人就是欠管”的理论家不少。但肯说自己就是活的太自由、没人管、或是太有钱、没人罚,所以才想开个车上街,想去被交警管管、挨个罚单的神经病,只怕一个都没有。

而在开车的过程中,随着车辆越来越多,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更方便、安全的出行,大家又不得不制定一套规则,这个规则就是包括红绿灯在内的交通规则。
所以在对交规的审视中,我们可以清晰看到,公权力的产生,是后天而非先天的,是先有了参与者的自由,而后才出现对其的制约和灌输的。交规执法权其实来自于所有出行者们自愿让渡出来的那部分权利,或者像卢梭所总结的“人生而自由,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”——你只有遵守交通规则的约束,才能享有自由出行的权利。个体的权利和责任是在这种动态博弈中完成了平衡和对等的。
而由于不同于其他的规则,交通规则很少受意识形态、民族意识等宏大叙事的干扰,它总能最完美、最纯净的还原一个“社会契约”应该是怎样的——
你看,大多数交通规则,都能符合行政学上的“比例原则”,既管理者只应为了保证公共安全和社会运转的最高效率,只执行最小限度的管束。
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马路上,都是对司机来说法不禁止既许可,而对交警来说法未授权不可为。
这一点在红绿灯上体现的特别明显:如果你看到一个十字路口是不装红绿灯的,那多半意味着这个路口车流稀少,司机的行使权完全没有必要由公权介入干涉,你们自己协调就好——这还原了一种人与人交往中最原始的“自力协调”状态。
而越繁忙、复杂的路口,往往要设立越复杂的红绿灯,这就意味着个体在这种场景中无法达成“自力协调”,驾驶者必须上缴一定份量的驾驶自由,由公权力代为完成这种协调。

可是这种协调,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必须遵循“比例原则”的——通常的路口只会设立最简单的三灯红绿灯,让驾驶者受到了最小的管束,以维持秩序。绿灯亮的时候可以直行或左右拐,红灯亮的时候也依然可以右拐。
而指使灯数量的增加,意味着你受管束的增多。九宫格红绿灯则达到了极致,司机在这样的红绿灯面前,驾驶自由被完全剥夺了,无论直行、左拐、还是右拐,必须完全等待这个管理者象征物的授权。

这种最严格的管理,一定只适配于最复杂、最需要公权力协调的路况,一旦脱离这种使用场景,它给人的感觉,就一定是拘束、压抑。因为所有人,都会在这个红绿灯面前感受到那种被管理时的拘束感、动辄得咎、和“被安排感”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孙正良老师开那个直播,从思路上就是错的——他力图阐述自己的这个设计有多么多么精巧、优美、多么“符合人性”,说服大家“时间长了大家就习惯了”。
但他忘记了,所谓人性,就是对这样严格的管束,无论适应多久,都不会习惯——他们只会在必要时接受。
而红绿灯,作为一种管理的象征物,在任何人的眼中,都不可能是美的,跟所有为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订立的规则措施一样,它只是一种“必要的恶”。
对于出行者而言,最美的红绿灯一定是最简洁、甚至不存在红绿灯,因为它意味着出行者可以在这个路口,在遵守基本交规的前提下,最大限度的享受自己的驾驶自由。
所以我觉得,虽然“新版红绿灯”只是虚惊一场,但这件事传达的公众审美共性,还是蛮靠谱的——
所有人都更欣赏那种越简单越好的,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管理规则。没有人会主动喜欢一种所有行动都需等指示,任何自主行为都动辄得咎的规矩,和由这种规矩构建的社会——哪怕那种规矩,只是你路口上碰见的一个繁琐、笨拙、呆板的九宫格红绿灯。
但,怎么会有那么多人,轻易据相信自己明天会被困在一条布满这种繁琐、过度管束的红绿灯的道路上呢?
这本应是一桩最疯狂、最违背现代社会常识的反乌托邦狂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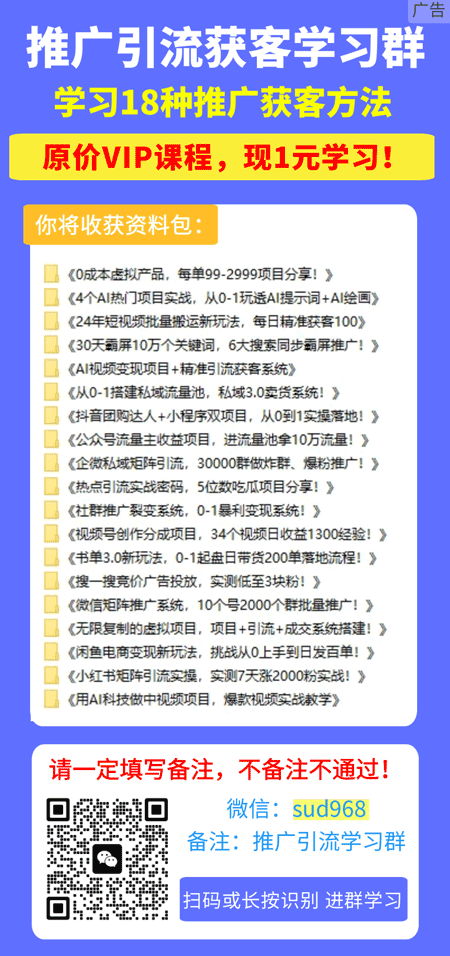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gooyie.com/41307.html
